第12卷第4期 总第405期
《红与黑》
——司汤达
汉语言文学233班 车丽娜 指导老师 梁莉冰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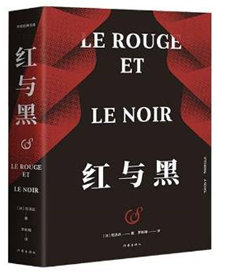
内容简介
在法国复辟王朝的阴霾下,一个木匠的儿子——于连·索雷尔,怀揣着拿破仑式的野心与诗意的敏感,试图冲破阶级的樊笼。他凭借过人的才智成为市长家的家庭教师,却与高贵的德·瑞那夫人陷入一场炽热而危险的爱情。命运的齿轮转动,他踏入巴黎上流社会,在侯爵的府邸中周旋,与骄傲的玛蒂尔德小姐展开一场理智与激情的博弈。然而,一封被胁迫写下的告密信,将他推向深渊。枪声响起,浪漫与野心在审判席上化作绝响。司汤达以冷峻的笔触,剖开一个时代的虚伪,让于连的悲剧成为永恒的人性寓言。
写作背景
19世纪初的法国,拿破仑的陨落让旧贵族与教会重掌权柄,而新兴的资产阶级仍在暗流中涌动。司汤达以1827年一桩真实的情杀案为蓝本,将时代的焦灼凝练成《红与黑》的篇章。红,是热血与革命,是于连心中未竟的英雄梦;黑,是教袍的阴影,是复辟王朝下窒息的秩序。司汤达亲历过拿破仑战争的辉煌,又目睹了波旁王朝的腐朽,笔下既有对往昔荣光的追忆,也有对现实冰冷的嘲讽。这部小说不仅是于连的挽歌,更是一面镜子,映照出人性在野心、爱情与命运之间的永恒挣扎。
精彩分享
1. “社会好比一根竹竿,分成若干节。一个人的伟大事业,就是爬上比他自己的阶级更高的阶级去,而那个阶级则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他爬上去。”
2. “为了治治你的心高气傲,就该让你招人记恨;而守正不阿,依我看是你唯一的生路。只要你毫不动摇,皈依真理,你的敌人迟早会慌乱自溃。”
3. “上帝之所以被人原谅,因为上帝是不存在的。”
4. “但是回答我的爱情时,她必须认为我们之间是完全平等的。没有平等就不可能爱。”
5. “一个年轻人在二十岁上,只要受过一些教育,他的心灵就会顺乎自然,爱情往往不过是一种最使人厌倦的职责罢了。”
个人感想
“难道我是个懦夫?”他对自己说,“拿起武器!”——于连·索雷尔。
当 《红与黑》走到最后一页,我的心情久久无法平静,有人赞颂主人公于连的勇气,也有人厌恶他的倨傲。可无论如何,他都是一个拿起武器反抗阶级的人,他拥有深沉的野心,也拥有真挚的爱情。读完这本书,我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小说人物的悲剧,我还看到了时代与历史的悲剧,看到了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悲剧。
倘若你拥有强烈的野心,想要跃升顶层的阶级,你选择卑躬屈膝乞求上层的施舍,还是选择以自己的聪慧拿着武器竞争。也许你以为于连选择后者,然而他两者皆有,在某些时候他自傲,在某些时候他聪明,有时候他又懦弱,有时又勇敢。于连是一个复杂的人物,他拥有着复杂的人格,他会在面对市长夫人时感到自卑,又会利用市长夫人对他的情感去逐利,可他又向往“平等的爱”;他会厌恶与仆人一同吃饭,又会对市长剥削民众感到忿忿不平,他渴求着“公平的社会”。当他尝试对阶级进行反抗,哪怕注定迎来失败和死亡,他也要大声嚷道:“我不过是个反抗自己卑微命运的平民”。
于连是不彻底的、不单一的,他是精于算计的野心家,也是为爱痴狂的浪漫主义者。与市长夫人的禁忌之恋中,我看到了他被压抑的情感喷薄而出;而在与贵族小姐的情感博弈中,又展现了他作为平民知识分子的骄傲与自卑。这种人物矛盾性超越了简单的社会批判符号,成为一个血肉丰满的形象。当他在狱中卸下所有伪装,我们才看清这个“野心家”内心最渴望的,不过是摆脱面具后的片刻真实。
司汤达对书中人物的心理描写达到细致入微的程度,我能够从中看到于连在行动中背后的想法,也能够一点点探查他心里的波动,甚至到后期能够完全窥探出他的想法。司汤达用这样绝妙的心理描写手法,将读者带入于连的内心世界,让我们去感受他的喜、他的悲、他的怒、他的痛,我们能够触碰到他的灵魂,有时甚至能够与之对话,当看到他站在法院发出震耳欲聋的质问时,书中情节升华到巅峰;当看到他死去的那一刻,这本书的悲剧性色彩也达到顶峰。
《红与黑》的书名本身就是一个精妙的隐喻。红色代表以特殊方式反抗复辟制度的小资产阶级叛逆者,黑色象征反动教会、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,这正是于连生命的两极。他渴望拿破仑时代的红色荣光,却不得不栖身于复辟时期的黑色秩序。这种分裂不仅是于连个人的,也是整个时代的。司汤达通过这个小人物的命运,捕捉到了一个转型社会的集体焦虑:当旧秩序尚未完全崩塌,新价值又未确立时,人该如何自处?
读完《红与黑》,我知道了一个再清晰不过的道理:当现实与理想割裂时,请拿起武器,请保持反抗的勇气!
作者简介
司汤达(Stendhal,1783年1月23日——1842年3月23日)。原名马里-亨利·贝尔(Marie-Henri Beyle),“司汤达”(又译斯丹达尔)是他的笔名,19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。代表著作为《阿尔芒丝》《红与黑》(1830年)、《帕尔马修道院》(1839年)。1783年1月23日,司汤达生于法国格勒诺布尔,少年时代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氛围中长大,崇敬拿破仑,并多次随拿破仑的大军征战欧洲。1814年波旁王朝复辟后侨居米兰,同意大利爱国主义者有来往,后被驱逐出境,回到巴黎。他的主要作品大部分是在1831年后写成的。1842年3月23日逝世于巴黎。
红与黑/司汤达 郝运译 I565.44/S703-2 上海译文出版社,2006. 馆藏地:社会科学二(东区三楼)